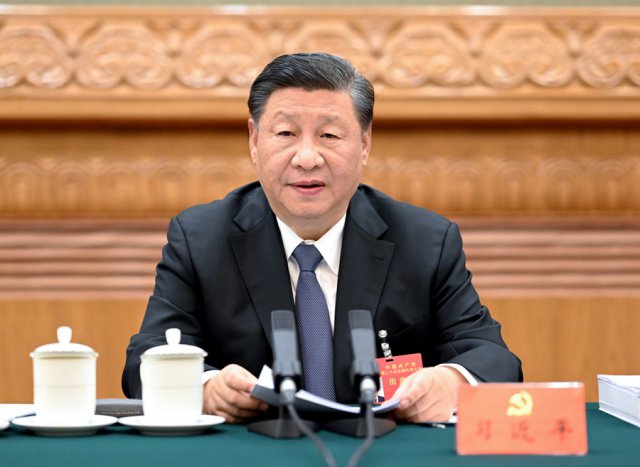2000年秋天,我的办公室里走进了一个黝黑干瘦的老头。他进办公室没说话,便一头蹲靠在角落里,从怀中掏出一只油光发亮的烟袋,边抽边叹息。一会儿,他抬起头,哆嗦着对我说:儿子因病走了,留下儿媳和三个女孩。因为给孩子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且欠了许多外债。要强的儿媳为了让三个女孩有一个好出路,低三下四四处借钱供孩子上学。每到开学时,就是他们家的“受难日”。眼下,大孙女宋霞光荣考上了平陆中学,但上学的费用还没有着落……
听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微微一震,耄耋老人、孤儿寡母、债台高筑,情况确实特殊,理应加以照顾。但全县这类情况太多,局里资金很有限,救济恐怕困难。于是我对老人说:这样吧,您先回去,明天我一准到你家看一看。
那天一整天,我的脑子里都萦绕的是老人一家的事。他们的困难深深地拨动着我灵魂深处那根救助的琴弦,于是我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千元,准备明天捐给为学费而伤心的宋霞一家。
尽管我事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老人一家的困难还是令我十分震惊。在尧店村的一条土沟边,老人一家就圪蹴在破烂的几眼土窑中。木门土炕,旧桌烂箱,土锅土灶,家里的陈设全是旧家具,炕上铺着缀着补丁的褥子。实话说,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过两千元钱。更令我震惊的,是宋霞母亲在小本上所记的账务,那一串串并不规整的阿拉伯数字,无不在诉说着家庭的窘迫和无奈。然而在他们身上,却洋溢着一种不屈服命运,自力更生的精神。年逾八旬的爷爷尽管年老体衰,但仍承负着繁重的体力活,而身体并不健壮的宋霞母亲,则主动到中医院里伺候病人,以挣得几个救命钱。对如此苦陋不坠青云之志的家庭,我们理应大力扶助。我当即掏出一千元钱,诚恳地递到面带忧虑的小宋霞手上,热情地对她说:“孩子,你就上学去吧,我虽然没有多的,但总有少的。况且,我身后还有各级党委政府呢。”
从此,宋霞一家的困难,就成为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情结。每到开学时,我和爱人就带着我的儿子、女儿来到她的家中,多的给三千元,少的有几百元。每到年终岁尾,我们一起拿着麻花、面粉、蔬菜、肉等过节的东西到她家慰问。他们几个姊妹的身上,穿着我捐助的衣服。我们用微薄的资助,微暖着宋霞一家的心,用热情的鼓励,鼓舞着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的爱心资助已进行了十三个年头。在这些年里,宋霞由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又由大学毕业挣得了工资。但他们家的穷困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宋霞妹妹的学费仍是摆在她母亲心上的困难。我们于是又开始资助她正上大学和高中的两个妹妹。资助似乎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成了我们奉献社会、热爱人民的精神支点,我们决心,只要周围还有困难群众,无论他是谁,我们都要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一如既往。
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爱心收到了可喜的双赢成果。每逢节假时,宋霞都要为我发来温馨的问候。每年春节前,她都要亲自为我送一包天津特产麻花。而令我收获更丰的,是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了解了农村,了解了生我养我的农民,知道了农村里存在着诸多的贫困和艰难。这些现象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两个孩子心中,使他们体验到生活的来之不易和父母为生活奔波的辛苦,酿成了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社会、奉养父母的勇气。它也促使我更加关注弱势群体,重视困难群众,利用民政工作努力为他们争利益,争资助。最令我高兴的是,共同的活动拉近了我和爱人之间的距离,它使我们更加温暖,更加挚爱,更加和谐。
我深深地感谢这个时代和我的工作,它使我拥有了这么一段颇有意义的经历,拥有了这样一种高尚的精神体验,它涅槃似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生活。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