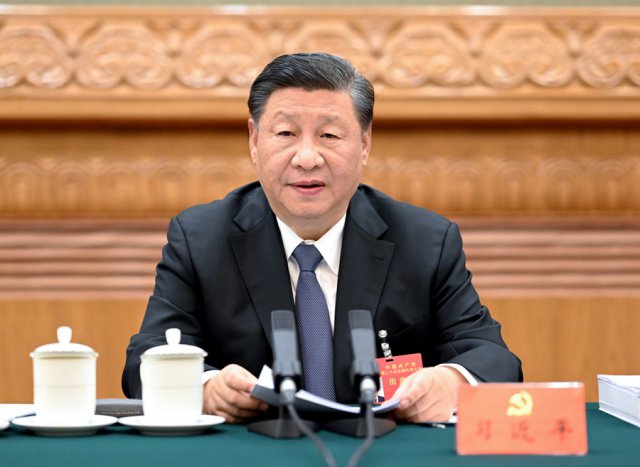面前是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背面是粉红色的、灼灼鲜艳的桃花掩映,左边有一望无际翻滚着绿浪的麦田,远处是刚经春雨洗刷后更加柔嫩的青山。暖暖的春风不断的吹来,缕缕的芳香悠悠地飘散……这就是母亲安葬的地方,一块令我哀思不尽的厚土。
在清明节这个令世人祭祀和怀念已故先辈的日子里,我又来到这里,来祭拜和看望我的母亲,带着满腔悲楚和无限的怀念……
母亲是位勤劳、节俭、善良的农家妇女,在娘家为长女,比我父亲大四岁。那年月俗兴早婚,母亲过门时父亲只有十二岁。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顺着黄河向东逃命。爷爷为了村里三十几条人命能保全下来,从山洞里挺身而出,惨遭日寇杀害。父母劫后余生,从东山深夜逃回,含泪草葬了爷爷。家也被毁了,门板和桌椅以及能烧的东西全被化为灰烬,院子里到处是弹坑,弹壳满地,唯一幸存下来的只有孔破窑洞和土坑。粮食被抢光了,全家人靠挖野菜度日。谁知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父亲在一次“抓壮丁”中虽逃出了虎口,却染上了日寇释放的细菌病,整日里血尿淋淋,面青唇紫,命在旦夕。为救父亲,母亲连夜爬过日寇几道封锁线,在古渡茅津找到了神医安永全,求得了几份中草药,总算保住了父亲的性命。
好不容易盼到日寇投降,却又遇到国民党匪军在争抢胜利果实。这时父亲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联村粮食干部,一天到晚忙于为解放前线筹备军粮。母亲一边养育几个儿女,一边纺线、做鞋、送弹药,支援前线,还亲自将两个负伤的解放军女战士接到家里养伤,直到伤愈归队。在参加革命工作中才知道,当年救父亲的神医原来是党的地下干部,连姓名也是代号,难怪“药到病除”。
解放后,母亲是全村第一批入社的社员,每年都要领回大红奖章,脸上的笑容也从未间断过。
进入“大跃进”、“食堂饭”的年代,贫困又一次降临。在我出生不到五个月的时候,母亲为使饥肠辘辘的儿女有口饱饭吃,忍痛割爱把我三哥送给了在运城吃商品粮的二姨妈。回来的路上恰逢隆冬,大雪封山。五、六十名旅客挤在一辆唯一通向平陆老家的、没有顶棚的卡车上。车上中条山,坡陡路滑,一车人全下来推车上山,唯一照顾母亲和怀中的我坐在驾驶室里。天快黑的时候,车总算到了张店,可离家还有五十里路。望着茫茫大雪,怀抱因没有奶水饿得哇哇直哭的我,母亲愁得两眼直淌泪水。一位好心的大娘端来刚排完队领到的两碗稀粥,母亲舍不得喝一口,赶忙端起来喂我。没想到,我小手紧抓碗边,一气喝完了两碗粥。看着我喝粥的馋相,母亲笑了,可微笑中却饱含两眼辛酸泪……
孩提时我曾记得,每到四月间,门前河湾里正是洋槐花盛开之时。一夜之间,白色碎花如瑞雪压枝,清香四溢。母亲就带着我早早起来去采花,采回许多许多的洋槐花,掺上一点点面,蒸着吃。就这样在贫困难熬的日子里挣扎。
夜晚,门外或雨、或风、或雪,母亲都在如豆的油灯下纺线,直纺到更残夜尽。
那年月吃的头等要紧。一入春,母亲就带着我去田野里挖野菜。拎只小筐,拿着小铲,在麦苗的缝隙间,在田埂上,瞪大眼睛专找“平平菜”、“羊妈妈”、“婆婆丁”,生吃得我满嘴发绿。母亲还教我辨认毒草和野菜,一种叫“勺子菜”的,叶端凹个窝,叶杆直直的,很像把勺子,我至今还记得。
煮饭烧的柴都是晒干的野草和苇叶。一到冬天农闲时,母亲就带着我随父亲一起到五里外的黄河滩上去割枯草,沙地上到处都是齐腰高的“马刺芥”、“蓬丫”,一会儿就割到一大堆。父母手脚都麻利,眨眼间用担子挑着就要走。我闹着要玩,要玩沙,玩迷藏,追野兔子。母亲护着我只得让父亲歇一会儿。我开始和邻家两个孩子一起在黄河边撒野,拼命的玩,引得越冬的灰鹤在水边时飞时落,高亢嘹亮的叫声不绝于耳。
我开始上学了,家里生活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在县城念高中时,穿的还是过去母亲纺织出来的粗棉布,城里学生讥笑我寒酸。家里又没钱买新衣,母亲只好买些染料在大锅里为我们兄弟几个每人染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穿起来到县城一试,比大街上那时髦的“绿军装”还绿,还新鲜。
在念中学三年间,因为家里困难不能在学校食堂吃饭,每天都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着咸菜喝开水,盼的就是星期天。那样,我就可以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母亲,就能回到冒着炊烟、处处是温暖的家。也总是在星期天,母亲借我回家取馍的机会,取出舍不得吃的白面,亲自为我擀两碗面条,加些油泼的葱花、豆腐丁,看着我吃得饱饱的。母亲总是这样把一切温暖与爱都给了儿子,呵护着我长大。
记得秋假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家里的电灯下写作业,窗外不时传来几处秋声,闹钟的时针已走向十一点。在我的身后,母亲正忙着为我洗衣服,衣砧声不时入耳。
忽然,停电了,只有一缕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母亲的脸上。我蓦地瞧见母亲的脸色显得格外的憔悴,连忙丢下课本扑了过去:“妈,您放着吧,让我来洗衣服,您快去睡觉吧!”
“你写你的,妈不累!”母亲一边说,一边找火柴,“嚓-”的一声划着,点亮了油灯,并向我投来一束期望的目光。
我知道母亲眼睛里的话,我更知道母亲心中因为没有文化而产生的痛苦和对儿女寄托的期望。为着母亲的心愿,我刻苦学习,自强不息。
贫穷能培育性格,困难可磨练意志。我常以此为戒,立志求生存,求进取。
斗转星移,事过境迁。党的富民政策终于使母亲看到了幸福的生活。责任田下放到户,老人的劲头更足了,每年打下的粮食两、三年也吃不完;过去一家七口人,一年到头只能从队里分到四两油,而今仅田边的油菜就能榨出一百多斤香油;那时辛辛苦苦挣得几千个工分折合下来只有二十几块钱,且多半领的是白条,如今门前的菜地和桃园,一年少说也能赚回五千元。家里生活也变了大样,每天都是白馍、大米,想吃肉随时都有。不像过去那样,到了春节那天,一人只能吃三个白馍,半斤肉吃得满家香。
母亲年岁大了,特别爱看戏。只要村里和邻村有戏,儿女门就轮流送她去看。到戏台下,买个粽子或油糕,买根冰棍或蛋卷,一边吃,一边看,津津有味。
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更谈不上去旅游了。我们想请她到大城市去看看,她舍不得花钱,怎么劝也不去。没办法,我们只好带他去三哥工作的运城,去关帝庙拜关公,去机场看飞机,去盐化瞧那一望无际的盐池;或是带她去一河之隔的三门峡市,到动物园看飞禽走兽,到百货大楼购物,到黄河乘大轮船。说是去带她看驰名中外的中流砥柱,母亲说:“不就是'娘娘河'、'梳妆台'前那座石山柱吗?逃难时常从那边上走过!”她始终没忘了过去。
我也忘不了母亲的过去和自己的昨天。每次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临走时,我总是面对母亲住的窑洞门楣上那一大串红辣椒凝视良久。因为,它不仅浓缩了以往的岁月,也浓缩了东方的太阳;它不仅储存了二老双亲的心血,也寄托了母亲对红红火火好日子的向往。
没想到,在母亲七十七岁那年,一场病使我们母子天各一方。面对母亲溘然去世,我心如刀割,呼天不应,哭地不灵,只有无限的悲楚与恸哭。面对母亲带着对儿女的牵挂和期盼的遗容,悲哀中,我泣问苍天:宇宙大能容万物,为何就容纳不下我亲爱的母亲;岁月长可无限延长时光,为何就不能延长我善良母亲的生命?
从此以后,人去屋空,那座小院再也没有升起的炊烟,那孔窑洞再也没有母亲的身影,那块故土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声音。苍天为母亲洒泪,大地为母亲悲恸,鸿雁为母亲哀鸣……
儿的泪还和往年的清明节一样的滚烫,妻的泣声还跟送行母亲时一样的悲切。“妈,我们来看望您。”磨砺中儿的志气越坚,进取中儿业有所长。母亲期盼儿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儿已成为业余记者和作家,所写的公文和新闻在省、市获奖,文学作品在全国获得一等奖;母亲期望儿不再为吃穿发愁,而今家庭殷实,生活水平已达小康;母亲牵挂子孙,如今的孙子孙女个个聪慧,知识和身体都在成长……生活随时代在提升,时代随国家在进步,国家在人民的奋斗中正在昌盛富强。“妈,您为儿高兴,为国家而高兴吧!”
砍来大把大把绿油油的松柏,采来一束一束正在盛开的鲜花,连同我永远的怀念和不息的敬爱,一起献到母亲的坟前:“妈,安息吧,明年再来看您!”
我永远忘不了的母亲!
(本文2003年10月入选《永恒的母爱》书系,并获全国二等奖。)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