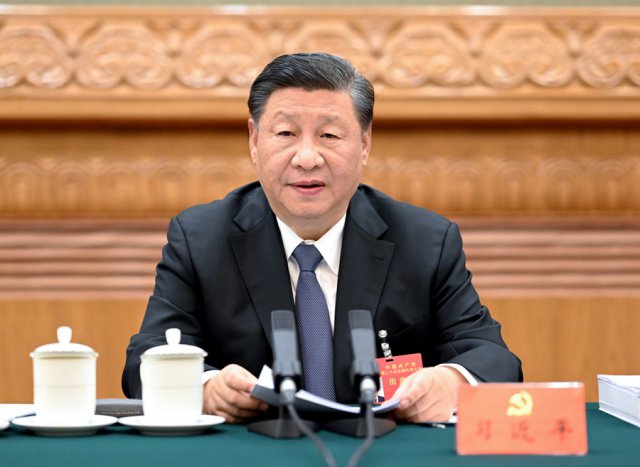几乎一夜之间,我彻底告别了走路一阵风、爱吹口哨、上蹿下跳、满口脏话等坏习惯,开始留意打扮、早晚刷牙、含蓄微笑,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语文课。尽管我的作文写得一塌糊涂,前言不搭后语,我却乐此不疲,充满了激情。
我还经常出入图书馆,抓紧一切时间,即使是在课堂上,也如饥似渴地捧着砖头厚的小说,这一切质的飞跃,都缘于语文老师。
我的语文老师是刚毕业的女孩,她只比我大三岁,却已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她身材修长,肌肤白皙,穿着得体的浅蓝色或洁白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像朵雪域圣洁的莲花。每当这时,我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如同欣赏一件稀世高贵的清代皇家御用花瓶。我呆呆地想:这世间竟有如此好看的衣衫,它连开口都没有,是怎么穿在身上的呢?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天衣吧。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浅浅的,说不出是什么芳香,这种芳香让我呼吸变得贪婪,心跳加快,瞳孔放光,脑子兴奋得只剩一片空白。
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遐想,看着简陋斑驳的墙壁,我心里特难受。我只好闭上眼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阳光、帅气、知书达理的男孩,和她一起读书,散步,聊天。我抱着幻想入睡,梦中几多欢乐几多惆怅,醒来后又添无限苦恼。
一次,在课堂上,她在读一篇学生示范作文,我盯着她的脸,目光呆滞,做着娶她为妻的荒唐大梦。她一抬头,满脸愠色,快步走过来,把作文本递给我:“你来读。”
我慌乱地站起来,哗啦,碰得桌歪椅斜,桌上的东西掉了一地,引起同学一片哗笑。我呆呆地站着,生怕她看出我的心事,脸涨得通红。
她毫不留情:“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下了课,我默默地踩着她的脚印,大口大口吞吐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身子轻飘飘的,感觉像在天上飞。她那柔顺的长发,随着她动感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着,轻撩我的心扉,我幸福得有些眩晕。我忍不住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问:“老师,你身上搽的是什么啊?”
她没有回答。我觉察出有些不妥,马上闭上了嘴巴。
她的办公室简单而整洁,她让我等她,她去洗手。我好奇地打量着,见桌子上放着一本包着书皮的书,我拿起来翻阅,却从里面掉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英俊帅气,笑得阳光灿烂。我一呆,忙把照片夹回书里,想逃走,脚却不听使唤,浑身发抖地站着,脑子嗡嗡地乱成一团。
她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你怎么了,病了?哪不舒服?我这里有药。我趁她找药之际,飞快地跑了出去,一口气跑出校门,穿过胡同,来到一片小树林,树林里静悄悄的,我蹲在一棵树下,哭得一塌糊涂。过了很久,我恢复了平静,回忆照片上兵的神采,他是那样的阳光、英俊,而我,哪里比得上他。我仰天长叹,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兵。只有兵才配和她在一起,而我……我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我突然冒出个邪恶的念头,我要拆散他们。对,就这么办。从此,我每天好几趟去门房,看有没有她的信件。
我终于寻到一个机会,把寄给她的信揣在怀里。不知为什么,我眼前总出现这样的场景。她在细雨中,撑着一把雨伞,守在门房前,苦苦等待兵的来信。她的眼神充满了期盼,待邮递员走后,她落寞的眼神划过我的胸口,我的心都要碎了。那封信像炸弹一样,让我坐立不宁。我常常在梦中,看见她从我身上搜出那封信,从此对我不理不睬。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面目可憎的跳梁小丑。信压在我心上,像重重的一块大石头。
我害怕见到他,连她的课都逃了。一连几天,我都躲在树林里,度日如年。唉,我总不能一辈子不去上课啊,我忽然心血来潮,把信送回去,将功补过。
我把信夹在书本里,趁她上课之际,心怀忐忑去了办公室。
天赐良机,办公室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像窃贼一样,蹑手蹑脚进了屋,飞快地把信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然后,又闪了出来。
我像遇到大赦一样敲开教室的门,我愣住了,站在讲台上的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老师。
同学问我,你到哪儿去了,老师找你好几天。
她哪儿去了?
老师调到县城去了。临走之前,她把这个给你。同学把一瓶香水塞给了我。
我拧开瓶盖,一股熟悉的清淡芳香扑鼻而来,弥漫在我的青涩年华。
(作者为北京市延庆地税局干部)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
| 百合花2014年1期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