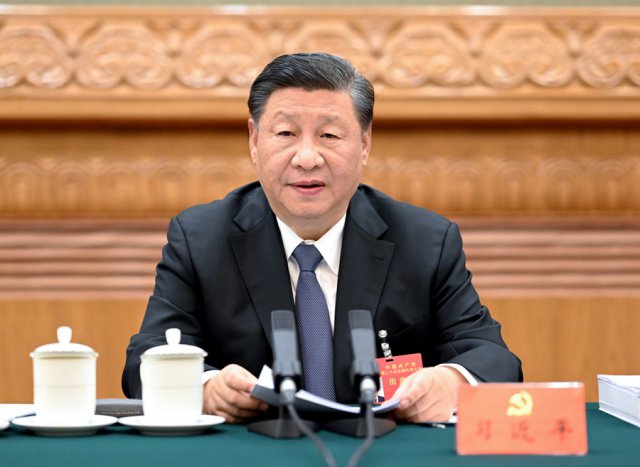(接上期)
第十三章 劳燕分飞
朝霞向大地洒下了万道金光,眼前的果园菜园,远处的野田和南屏山,像是凭借了凤冠霞帔的装点,更加美不胜收。这“车到山前必有路”不正是人们的口头语吗,这“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并非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美好愿望啊!水华除了这样安慰自己,她当然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仰或是抗争。
他们仨来到了菜园,卫超凡自然早就溜了。泡桐树下,他们击毙恶狼的地方,早已覆盖上了倭瓜蔓。水华和彩彩的手握得紧紧的,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凝重。昌翔扒开了倭瓜蔓,原来,盖住的只是狼的血迹。至于两只死狼,二女随着昌翔的目光,望向竖井。
这卫超凡竟和凌十二的做法不谋而合,死狼扔到竖井里就成了永久的秘密。这一老一少都是悄没声地舍弃了狼肉和珍贵的毛皮,生怕“打狼英雄”的光环罩住了自己。凌十二是韬光养晦,怕人说他“气焰嚣张”。卫超凡呢,要是被人发现他暗夜里在菜园活动,那还不等于发现了他在密切关注着古墓?他当然不会留下和恶狼搏斗的蛛丝马迹。还有一点,卫超凡是一万个相信昌翔他们,他们哪会揭发他?尽管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打狼救人英雄,但却决计不会宣扬自己的。
昌翔又想,也许下面就是狼窝呢。到这秋冬季节,不会再有暴发的山洪流经下面的涵洞。这样避静的所在,狼当成现成的巢穴也不是全无可能。那么,死狼抛下去,活着的狼自会当作美餐。设若如此,他们就难免会有一些考虑不周的遗憾呢。可如果他们已经把“盘踞”在下面的恶狼消灭殆尽,其“残部”也就不足为患了。不过,他没对水华和彩彩说这些,心里盘算着虽不能放松戒备,但却不可自相惊扰。
水华的接生技术也掌握得真快。有时,兴云老太稍加点拨,她便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比方说遇到了难产,老人家也不是全凭麝香海马等名贵药物,有时也用燕麦,百草霜(锅底灰),皂荚等毫不起眼而又农家不缺的东西。总之,如果不能顺产,也要分各种情况,比如临产阵缩无力啦,横生或倒产啦,胞衣不下啦等等,这要看产妇的体质强弱来采取最佳的方法。当然,有时候仅凭药物是不行的,那就要当即立断,采取内倒转术和外倒转术等手法。尤其是内倒转术,那是要把手伸进产妇腹内施术的,尽管十分复杂繁难,但水华也进境神速。兴云老太本来择徒甚严,她主要是看中了水华的纤纤玉手,也觉她看上去就很有灵气,想不到她的心灵手巧还是大大地出乎意料,能不惊喜莫名!
有时还要用一些特殊的药物,比方兔子脑啦,螃蟹脚爪啦等等。兔子对水华来说,是何等的可爱呀,但却要砸碎它的脑壳!那螃蟹虽然“横行”,但要把它的脚爪捣成浆,也未免太残忍太霸道了啊。幸好这类事儿有产妇家里的人去做。尽管如此,水华心下还是难免惴惴。
接生最常用的药物,还数黄酒,兴云老太酿造的黄酒,掀开瓶塞,闻一下都会醺醺欲醉。当然,产妇家里也多数酿有黄酒,但他们的技术和兴云老太一比,未免小巫见大巫。水华想到“大巫”这个词儿就觉好笑,干妈她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巫”啊。老人家本来“两专多能”,以“稳婆”和“巫婆”的精湛技艺享誉梓里,如今竟能在自己的劝说下忍痛割爱,丢掉“巫婆”这一特殊爱好,不禁莞尔。
水华由于婚事揪心,俊俏的脸上常是笼罩着一抹愁云。而最开心的时刻,也就是她们接生的胎儿呱呱坠地的时候。或响亮或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对她来说,无异于最美妙最动听的音乐。这不唯是受到产妇一家欢乐气氛的感染,更是她打心底里就喜欢小孩呢。
村里人嘛,难免有重男轻女思想,生下女婴,经常是产妇会像做了错事一般局促不安,家里人也有不豫之色,水华就抱起婴孩轻轻地唱道:“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妈的小棉袄……”这样,产妇及全家都会笑逐颜开。
然而,水华一回到家里,烦心事一下子就攫住了她,当然是妈一个劲的唠叨,她多数时是好说,要水华嫁卫超凡,好说不能奏效,便使出了撒手锏:她竟不服用水华精心配制的丸药了,而改服卫超凡的药。
这可乖乖不得了,这下子该水华求她妈了。但当妈的也坚决不让步,并怒道:“你管我是死是活,就算人家药里有砒霜,我也认了,大不了是个死!就算让毒药毒死,我也不愿叫人气死。”
这一回,母女俩正闹得不可开交,水军骑车回来了。他来取面,也顺便带回一些菜。姐和妈正憋气,没人理他,爹在一旁抽闷烟。水军不断地问,才从爹口中得知,姚铃儿的爸妈答应女儿嫁他,但前提竟是姐姐必须先嫁给卫超凡。
怎么办?水军想,迫在眉睫的事儿就是离开水库。他心急火燎地又赶到水库,什么都不管不顾了。逮住姚铃儿就大发脾气:“让我姐必须嫁给卫主任那狗崽子?你爸妈还不是听你的主意?你敢说你不是周技术员的傀儡?周技术员还不是卫主任的走狗……”
其实,这可真是冤枉了姚铃儿,周叔不过是希望她能嫁水军,并且许她过门后可以担任水委会的出纳员,这宗“交易”不过仅此而已。至于要水华先嫁给卫超凡她才能过门云云,那是卫贫协给“一阵风”下的指令,“一阵风”不负重托,说通了姚铃儿的爸妈,才抛出了这桩霸王条款,姚铃儿其实并不知情。
可水军盛怒之下,如何能听进姚铃儿的辩解?何况,趁势离开水库也是他最好的选择。他寻思,哼,凡事还不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走为上计。
一下子带走自己的全部东西,自然不能。他拣最主要的、也就是“标志性”的东西——铺盖卷儿。“卷铺盖回家”嘛,任谁都明白这是甩手不干了。
这当儿,姚铃儿自然明白无论是循循善诱还是疾言遽色,都是不行的了,便赶紧“喀嚓”一声将车子上了锁,抽出了钥匙。
水军一愣,说道:“好,车子是公家的,我不过是怕丢了,想先骑回家。你愿管这事,很好。”
他背起铺盖卷,头也不回地走了。姚铃儿赶紧跑回村里,请四爷爷先照看水库,便急忙骑车追赶,不一会,便赶上了水军。
水军道:“你还是请回吧,八匹马拉我,我也不干了。”
姚铃儿道:“这……我陪你回家。”
但水军死活不接姚铃儿的车子。背上铺盖卷躲来躲去的,姚铃儿又不依,两人在路上,像是争吵厮打,路人均以疑惑的目光注视,有一个热心肠的老者竟来劝解。水军见不是头,只好让姚铃儿抱起铺盖卷儿,自己骑车载她回家。
又回到家里,水军就知道妈这一关不好过。当妈明白儿子是要扔掉工作,而姚铃儿是来追他回水库时,便沉下了脸,一个劲地数叨水军。对姚铃儿呢,又马上笑脸相陪,直骂水军这小畜生任性胡来,又直夸姚铃儿明理懂事。
但要赶水军重返水库,无论一家人好说歹说,终不能奏效。姚铃儿的爸妈已经由吴四告知,女儿回了未来的婆家,故放心得很。姚铃儿也就住在水军家里敦促,心想,这“相持阶段”决不会旷日持久,“反攻阶段”已指日可待。
果不其然,没几天,姚铃儿他们又来了强援——瑶菁和小楚小两口儿。而引这小两口来的,竟是宫兴,他虽和水华住一个村,但轻易不来往,也算稀客,瑶菁小两口更是初次登门。这瑶菁虽说和姚铃儿、水军都有不错的交情,但水军觉得,她来的目的,定是劝自己回水库坚守岗位,这还不明摆着是来帮姚铃儿的!
这下子,本来就势孤力单的水军,更隐隐地感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
原来,又轮到下疃浇地,自然还是罗姐和瑶菁“看渠”。她俩见到吴四老汉又重返水库,不禁大奇。吴四老汉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请求她俩劝说水军回来。罗姐还没表态,瑶菁便赶紧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样子,满口答应。
下疃大队浇地不过一天半时间。瑶菁回到家里,急忙携同丈夫小楚来到屏底村。原来,上次浇地后,罗姐就催了小楚几次,让他去屏底找董高看病,小楚嘴里应承,却下不了决心,这种病如何对医生言讲?保健站是公众场合,当着多人的面更难启齿。瑶菁也催了丈夫几次,可他还是一味搪塞,故而拖了下来,一直未能成行。
这回,瑶菁终于说通了小楚,也多亏了敦促水军重返水库的使命迫在眉睫,小楚便不再推诿搪塞。小两口先到屏底保健站求董高诊治。董高诊断为“肾阳虚”,这种病对他来说,自然是成竹在胸。一来是治疗的需要,再者小楚是外村人,来回跑的次数多了,也耽搁时间。董高就给小楚确定了先治标再治本、先峻补后缓补的治疗方案。具体说来,就是先服用三副汤剂,再长期服用丸剂,那丸剂是董高的经验方,叫“五肾丸”。除有二十多味中草药外,还有市场上绝难见到的五种动物的“肾”。这里的“肾”,可不是指肾脏,而是传统医学里称为“外肾”的东西,也就是动物的睾丸。哪五种动物呢,驴、鹿、牛、羊、兔是也。
这“五肾”,别说各村保健站没有,就算到镇子上,甚至跑到市里,也未必能买得到。
董高开好了方子,见小楚和瑶菁面有难色,便说道:“找宫兴呀……怎么,不认识?”
瑶菁看了小楚一眼,两口都乐了,哪能不认识呢。这宫兴很多日子都是骑上车在各村转悠,有一次,他转悠到下疃村,刚好瑶菁几天前从集上买回了两只猪崽,便请宫兴给去势。这个可不比兴云老太和水华她们接生,经常是劳心出力大半天,胎儿才呱呱坠地。只见这宫兴来到猪圈跟前,一绰手便抓住一只,他用牙咬住小刀背,手一捏,便捏住了睾丸,一刀划去,再一捏,挤出两个睾丸,妥了。另一只是母的,也是如法炮制,便割掉了“花肠(卵巢)”。阉割一只,也就是打个哈欠的工夫。小楚当然知道本村哪几家刚买了猪崽,便引着宫兴挨家跑,一袋烟的工夫,五六家的猪崽都干脆利索地阉割停当。
小两口寻到宫兴家里,可铁将军把门。问邻居,都说要是以前,他多数天黑就回来了。可这两年,却是吃不准的。他经常是两三天、甚至四五天才回来一次。
小两口点头。可不是,现在,宫兴不是也不常去他们下疃了吗。
瑶菁说小楚,就等着,难不成还要人家找咱吗?他如果回来不停又走了,再见他也不知要等到啥年月呢。
这个宫兴,要是前几年,他总是本着节约的原则,把弄回来的动物睾丸或炒或煮,总之胡乱弄熟吃了。
久而久之,他渐渐地身子有了明显的不适,但他没认为这是一种病。他想,人常说嘛,一辈光棍好打,半辈光棍难打,也许离异的青壮年健康男子,惯常都是这样的“蓬勃向上”。
但渐渐地,他感觉不对劲了。他本来体壮如牛,但现在却有了几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毛病,除此之外,还有失眠多梦,心慌盗汗,身疲乏力等症状。不得已,他找上了董高。董高的手指一搭上他的脉,便“咦”了一声,表情竟骤然凝重起来。
医生知道了更好,省得说给他听的。这种病,讲给人听能不难为情?
董高经过一番脉诊舌诊之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宫兴讪讪地,低声说道:“这……半年了?也许一年了?咳,谁记得清,也许还更早一些。”
董高安慰他说,这种病叫“阳强”,但毕竟不是真的强壮,而是肾阴虚的一种表现,吃几副药就好了。
董高好像知道他吃了过多的动物“外肾”,嘱他以后这些东西尽量少吃或不吃,晒干后备用,说不定还能帮别人。
宫兴心想,嗨,我如果学艺不精,主顾不多生意清淡,没有那么多扔了未免心疼的“副产品”,反倒不会得这种令人尴尬的病了。
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彻底错了,得这种病的人并不鲜见。不过,一般来说,症状都没有他这样明显,病程也没他这样长。更主要的是,别人哪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又不从事这种产业,又何来这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副产品”?何况一般情况下,许多小灾小病只要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像宫兴般地一味“火上浇油”,人体固有的不可小觑的平衡调节能力,也在拼命地纠偏以求自愈呢。
宫兴在董高的精心治疗下,一两个月便彻底康复了。不过,他虽然生理上的病症没有了,但内心深处,却更加思念他原来的妻子——那个叫做入画的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的女人。
六年了,按说,六年来,除了劁猪骟牛这类事儿,尽管忙碌,他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至少可以娶妻生子呀。况且,越是忙碌,说明他技术好赚钱多,找对象应该更容易。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推掉了唾手可得的好姻缘。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他的心里,除了他的入画——或是应叫做如画或如花——再也装不下别的女人。
他清楚地记得,她有时写“如”,有时写“入”,他便笑着问她,到底是哪个?
她也笑,柔柔地说:“就写‘入’吧,好写的嘛。”
他心里纠结,因为村里人给她起雅号,叫“八画”。起因是分红时签名,她签的“入画”。跟前不知谁说了声“八画”,大家哄笑,这个雅号就叫开了。
其实,在宫兴看来,她不光签名,她对任何汉字的书写,都再规范工整不过,但村里人的水平嘛,大概认为“八画”和“入画”这两个词相比较,还是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
村里人嘛,这样的内容作为劳作暇余的谈资,已经是很高雅很文明的了。但宫兴仍不愿让妻子受到这样的“礼遇”和“关注”。
于是他便问她:“叫‘如花’行吗?”
她又轻轻地浅浅地笑了,这样的笑,也许是最恰到好处的,足以荡人心魄。她柔柔地说道:“貌美如花?哪里话哟。笑靥如花?没有的嘛。”
他乐颠了,拍手笑道:“是的是的,有的有的。”
她还是轻轻地说:“还是叫‘入画’吧。哎,我本来叫解放,上学了,班里六个“解放”,老师就为我改成了入画,大家都说改的好。”
他俩分明是卿卿我我、举案齐眉的恩爱夫妻嘛。
是的,如果没有鲍老师的出现,也许他们直到现在、甚至直到若干年后的进棺入土时还是人人艳羡的恩爱夫妻!
然而,他们屏底当时是公社丁主任的蹲点大队,丁主任聘请来了市美术学校的鲍老师,给屏底村的影壁上画《大海航行靠舵手》。
村里人哪见过大海?万吨巨吨也是从书报上才有所了解,便围拢来看。但大家都是忙忙的,看一会也就走了。一天里多数时间都围在这里的,大都是一些带孩子的老头子老婆婆,他们也不是专门来欣赏画的,只因这里是村里的热闹地方,就算没有鲍老师在影壁上施展丹青妙手,这里也是他们含饴弄孙的首选场所。可入画,就完全不同了。
她每天来看鲍老师画,他画得那样认真,画出来的大海和轮船又是那样的逼真。她看得挺专心挺入迷的,像是他的学生。他这次下乡作画没带学生,但看她的着装打扮,肌肤和气质,都像是城里的女孩子,比他的学生还更像学生。
他好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刚回答,他马上便在影壁旁的黑板上写出来了。她惊异,他没有写成“如画”,也没有写成“如花”。她在他心里,是那样的纯真和高雅。
他端详着她,他完全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她竟完全理解,觉得他并没有丝毫庸俗的甚或是邪恶的念头。
他喃喃地说道:“入画,入画,可真是堪入画呢,可也真是难描难画。”
她脸红了,她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在夸她,
他说她:“我回到学校后,有了时间,就给你画一幅肖像,托人捎给你。”
她笑了笑。她觉得不好回答,她竟隐隐觉得,这样巴巴地捎来,好像有些欠缺,有些不够味的感觉。
这个大影壁实在是大呀,他足足画了半月有余,才大功告成。可离开时,他们双方竟都觉得离不开对方了。
但如果宫兴不放她走,不办离婚手绪,他俩想如愿,也没那么容易。
但宫兴对她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子,问她:“你想好了,不会后悔?再过一百……永远都不会后悔?”
她低头不语,那神情明明就是默认了。
事后,村里人当然对宫兴的态度是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了。有的人竟说,打坏他一件也不亏。也有人议论,宫兴只有利用特长,阉了他才解气。可宫兴呢,他有时也后悔,尤其是董高治好了他的阳强,他就寻思,农村人的女孩子嘛,差不多都是婚后两三个月之内就有喜了,而他们夫妻间的功课几乎是一天都没拉下,可她的小腹却一直没动静,他就该带她找董高诊治了,说不定会药到喜来了呢。如果有个一男半女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她也许就不会弃他而去了呢。可后来听说她和鲍老师结合后仍未生育,也就释然了。嗨,这董高又不是神仙,又不是送子菩萨,找他治,弄不好只会坏了他的名头。
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宫兴对这个入画的相思竟是刻骨铭心,从此再不婚娶。凭他的技艺和品性等等诸般条件,别说二婚,就是黄花闺女也有不少看上他的,但他却心如止水,不为所动。
他本来只在本公社走乡串户招揽生意,要是逢集日,人们就准能在鹰击镇熙熙攘攘的大集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有一天,他却心血来潮,把这些相当巩固的生意地盘毫不吝惜地丢了扔了,到距市里最近的云崖公社招揽生意。
四十里路程呢,他不嫌辛苦。生意忙了,当天赶不回来,他偶尔也到市里住旅馆,但多数还是住在农户家里。免费割骟换取吃饭住宿,再方便不过。他想通了,就算赶回家里,家里又有什么?自己到了哪里,哪里不就是家么。
好男儿四海为家,宫兴觉得这种见解实在是高超。他想,把自己算入“好男儿”的行列,也不能算是自我标榜吧。
他终于打听到她和鲍老师的家就在市西郊的云崖公社鲍原村,近市郊的村子都是大村,这鲍原村也不例外,和市区仅隔一条小沟。
原来,他这个行当除了赚钱较一般人容易外,还有另一种最大的好处就是消息灵通。
他知道她已参加了工作,在市工农兵艺术馆的文艺宣传队里当演员。他也曾偷偷地挤在观众堆里欣赏她的演出。她的翩翩起舞和嘹亮歌声,那足以夺魂摄魄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浪高一浪的阵阵掌声。他有时也想,自己娶了她,真等于把美丽的黄莺关在了笼子里,不惟大煞风景,简直暴殄天物。她跟随了鲍老师,郎才女貌不委屈啊。鲍老师熟人多交际广,为他联系了工作,她才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俩在一起,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和欢乐啊。
在路上,他也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她就像受惊的小兔,老远就躲开了。他觉得她是明智的,咱明明没有和她重修前好、破镜重圆的奢望,但是别人看见,你们两人秘密会面,怎能说不是藕断丝连?甚至还会说她脚踩两只船什么的——那可就是在给她身上泼脏水了。
还有一次,是他看见她和鲍老师两人推着自行车在路上慢慢地走,他却赶紧悄没声地躲开了,就像是做了天大的亏心事一般。
尽管如此,他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就算再也无缘见到她,但心理上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何况也真的离她不远呢,多跑点路就算辛苦些,也值啊。如果现在还让他像以前一样,业务活动范围仅局限于他们鹰击公社,他会急疯的。
这不,苍天不负有心人,他又遇见了她。
奇怪的是,她没有躲他,还好像是专门在等他。
他迎了上去,讪讪地,仿佛是他对她不住。她款款地迎了上来,仿佛有着重重的心事、深深的隐忧。
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狠狠地揉了揉眼睛,猛猛地掐了掐臂膀,生疼,不是梦境,不是幻觉,果然是他的……但现在已属于别人的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的入画。
她好像清减了许多,眉宇间似乎隐藏着忧思愁绪,更显得弱不禁风,楚楚可怜。
她怯生生地问他:“你……还好吗?”
他待要回答,却发现不论怎样回答,也就是无论说好或是不好,都会辜负了她的善意,甚至会对她造成伤害。
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道:“我……还好吧。老样子,将就着,一天一天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她欲言又止,却泫然欲涕。他猛然省悟,她一定有烦心事才找我,她必定有一个必须找我的充分的理由……
他关切地说道:“我……不知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他分明看见她眼里闪现着希望的火花,但一霎时,那火花又渐渐地在熄灭。
天哪,他见她犹豫,想到,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莫非是不想当“好马”了……
但他又马上觉得脸上一阵发烧,他恨恨地在心里骂自己,哪会有这样的事?她离开他时表示过永远不后悔的,她不是没主见的人哪。
他赶紧抢着说道:“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
下面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没有说出来,但他那斩钉截铁的语气和跃跃欲试的神态,却给了她极大的信心和鼓舞。
他幽幽地说道:“一个叫岑晨耀的权贵想占有我,我岂能屈从!我现在对鲍老师,就像以前对你一样,我的贞……一切,只能属于我的男人!他便诬蔑鲍老师为咱们村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隐含“恶浪攻击红太阳”的内容,是反动黑画。鲍老师也被定为反动黑帮,住进了学习班。
人们后来常说的关进“牛棚”,当时的说法就是进了学习班,被关押的人多数是被认定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
宫兴关切地问:“多长时间了?”
入画说道:“都关了半年多了,我找那个岑晨耀辩解。他说只要咱们村的贫下中农认为不是反动黑画,鲍老师就算无罪。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认定咱村的乡亲们对我和鲍老师必然反感、敌视。唉,他估计的也没错,我能找谁呢,想来想去,觉得也许只有你才肯帮我……”
她捕捉到了宫兴疑惑的神情,又说道:“岑晨耀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同僚,也就是革委会一班人都在场,想来他是无法食言的。”
她的腋下夹着一块红布,便展了开来。
宫兴看那红布,幅面足有四尺,长度也是四尺吧,方方正正的。她双手捧着,高高地举起,她的珠泪纷纷跌落在上面,一滴一滴竟仿佛是血的颜色。
宫兴和她一齐捧住了红布,只见上面用水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鲍邦彦是一个好同志,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战友。他饱含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为我们大队影壁上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轮红日在海平面上喷薄而出,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万吨巨轮迎着朝阳长风破浪高歌猛进,昭示着我们在奔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所向披靡永无阻挡。我们贫下中农看着这幅画,心潮澎湃,豪情万丈,“过黄河”“跨长江”斗志昂扬,勇创辉煌。
鹰击公社屏底大队贫下中农
他现在才知道那个曾经让他切齿腐心、痛断肝肠的大画家鲍老师的名字叫邦彦。
这是和入画一样美好的名字啊。
这样大的红布,写的字只占不到五分之一的面积。宫兴想,全大队的贫下中农全都签上名也占不满。
她孱弱的身子好像真的弱不禁风,在轻轻地颤抖。
他好想扶住她,她也好像要扑在他的怀里,但都克制住了。他们离得很近很近,但终究没有拉近距离为零。
他暗下决心:你放心啊,我就算去跪着求咱们村的乡邻,也要让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他接过红布,小心翼翼地收好。又看了她一眼,便骑上车,往回急奔。
水军逃离樊沟水库的事儿,几天来,村里传得沸沸扬扬。
不是吗,他们家的光景本来实在不怎么样,自从水军到樊沟水库上了班,一个跛子,竟谈了姚铃儿这样好的对象,好像真的是天定的好姻缘。有些人千挑万选,结果还说不准选了个“漏漏灯盏”呢,可姚铃儿这个百里挑一的女孩子,竟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这个“传奇”,偏偏是全凭卫超凡一家的鼎力支撑而产生的。笑你贫恨你富的人哪村没有?屏底自然也不例外。有羡慕的自然也有嫉妒的,现在,他们家又将做梦似的回归原来的位置,这样的大起大落,这样戏剧性的变化,怎能不为人们津津乐道?
俗话说,一人传实,十人传虚。闲话传来传去,有些人窃窃私语的竟是水军被卫主任开除了,姚铃儿赖在这里闹退婚,水华妈也气得旧病复发,已经不能起床云云。
“开除”和“退婚”当然是瞎说白道,水华妈的病当然也没那么严重,但身体状况却是一天不如一天。要是一直这样下去,重病卧床怕是很难避免。
水华和干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强颜欢笑。可兴云老太是何等样人,凭她丰富的阅历和高度的智慧,凭她对干女儿的关心,还不是了然于胸。她如果还不赶紧为干女儿做出重大决定,难不成眼看着她一天天憔悴下去?
兴云老太终于鼓起勇气向水华说道:“孩子,你和你的那个昌翔,一起走吧。先领了结婚证再走,走得远远的。”
水华岂能没想到这节?不领结婚证就出远门,两人在外地会困难重重;领了结婚证而不出走,却无法在家里、村里立足!
她轻轻地点头。老人又说:“不要埋怨你妈,她受的煎熬比谁都大。如果我是你妈,也只能狠下心来让你嫁卫超凡,她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走吧,树挪死人挪活,钱和全国粮票,还有省粮票,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水华再也忍不住了,抱着干妈失声痛哭。
老人忍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强笑道:“昌翔给人修剪果树,你给人接生,混他个三年五载都不成问题。但也不能在外耽得太久啊,最好别超过一年,你们有了小孩,还得回来上户口啊。还有,我和你妈都惦记你,你也惦记我们啊。但时日也不能太短,如果停不下三五个月就急着跑回来……就怕是瞎折腾白忙活了,记住了吗?”
水华赶紧找到了昌翔,想不到昌翔却掏出了一封信,他递给她时,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水华心里一咯噔,他这……简直是英雄末路的悲哀。
她终于鼓足勇气,展开了信。尽管水华也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还是双手颤抖,甚至连心底都在发颤。她只觉得天旋地转,脑海里像是有一整箱蜜蜂在嗡嗡乱飞……
尊敬的水华:
只这“尊敬的”三个字,就已经使她如五雷轰顶了。她现在才发现,“尊敬”和“亲爱”两个词的涵义,在有的时候,竟然有天渊之别!
她定了定神,还是硬撑着读下去——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看似老生常谈,却也不失为至理名言。
我们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有些事情是无论无何也勉强不来的。
我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这件事却实在无法表现出惯常所具有的果断的刚毅。只因为我总希望能有奇迹出现。我也在不懈努力,不断挣扎,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现在,我如果还不敢主动承担变心和提出分手的责任,那我非但不算一个好人,简直就不是人了。
我幼失怙恃,但所享受到的有限的母爱,直到如今,直到永远,都刻骨铭心!不揣冒昧,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我就是舍弃生命,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遑论是你的、也是我的最最亲爱的母亲。
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坚持要娶你,水军就会丢掉报酬丰厚的工作,也会失去人人羡慕的姻缘,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会有侥幸的。他明明有着甜蜜的爱情,光明的前途,却由于我的自私而不得不由幸福的巅峰跌入痛苦的深渊,这哪是我的作为?这简直就是强盗的行径。
再说你妈的病,你比我更清楚,家里要是陡遭变故,她孱弱的身子如何能挺得住?如果她的健康状况因而每况愈下,最终有个三长两短,我万死难赎!然而,无论无何,我却必须要坚强地活下去。你不是说过吗,如果我死了,你也不会独活。所以,我要永远为你而活着,正如你也是永远为我而活着一样……
看到这里,水华早已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她想到,人常说的千古艰难唯一死,却不料我竟失去了死的权利……我如一横心去了阴间,他也不会再留恋阳世。
如干妈这样的智者,竟也想不到她的精心安排会彻底落空。
她望着他,但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
她走出了果园,才想到自己少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我嫁了别人,你什么时候结婚?”
如果问出了这句话,昌翔也许会给她一个承诺。
但她一犹豫,终于没有折回去再去找他。也许就是这一犹豫,误了他,也害得自己还将长期为他的痛苦而饱受折磨。
瑶菁和小楚也还算幸运。
要是往常,宫兴就算回家,一般也是入夜时分了。今天他应承了入画的事,急于星火地赶回来,日头还老高呢。
小两口迎住他,说是因治病而前来找那些物事,宫兴笑道:“这还真是别处罕有,咱家不缺。”
说着,他从房檐下取下一个篮子,里面就是他积攒的那些物事了,多数已经风干。也有半湿不干的。他全倒出来,说道:“要是不够,我再攒。”
小两口要付钱,宫兴死活不收,小两口称谢不已,收好后便向宫兴打听水军住哪,宫兴喜道:“跟上我走好了。”
其实,宫兴要找的是水华。他骑车往回赶,一路上却在寻思,咱在村里也是受尊敬的人咧,可是要求乡邻为解救鲍老师的困厄而签名,大概得大费唇舌。耽搁时间久了,入画怎么办,她可是度日如年呀。时间拉得长了,卫贫协必然会知道的。老人家如果横加干涉,这事儿八成要泡汤。
记得入画刚抛下他的时候,卫贫协就当着他的面骂道:“这一对可恨的狗男女,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现在“狗男女”遭到了报应,卫贫协肯定觉得老天开眼报 应不爽。谁要是帮这一对“狗男女”,老人家不阻挠才怪。
可是如果水华出面,情况就会大大不同,说不定卫贫协看在她的面子上,就三缄其口置身事外了。这不正是人们惯常说的柳木锯牛角,一物降一物吗?
更主要的是,水华的心肠好,入画是好人还是“坏人”,她定然不会放在心上。她只会觉得入画是一个可怜的值得同情的女人,这个女人现在有了难,理应为她略尽绵薄之力,而不应作壁上观甚或落井下石。
当宫兴领着瑶菁和小楚来到水华家里时,水军自然大吃一惊。他还没反应过来,瑶菁就连珠炮似地朝他发了威:“你是不是革命青年?你难道没有学过《反对自由主义》?就算你要撂挑子,也得经过水委会批准,对吧。你要不信,咱们出门问问,十个人准有九……十个说你不对,咱打赌,你敢不敢?”
水军无言以对,瑶菁又继续说道:“你要是还不走,我们可要请罗姐来了啊……你要是认为罗姐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你提溜到樊沟水库?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她嘴里说着,手也不停闲,竟一把抓住姚铃儿,说道:“我们会把这个鬼丫头绑起来,你什么时候答应回水库,我们就什么时候给她松绑。”
水军明知道她是吓唬,但还是不由得着慌,忙道:“要文斗不要武斗,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这会儿,宫兴已经让水华看了那个鲜红的包袱。水华一看上面写的字,就大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何况,宫兴又不厌其祥地将鲍老师负屈含冤、入画请求帮助的事说了一遍。
水华也觉凄然,说道:“我虽然没见她,但也能想象得到,她陡遭变故,很孤独很无助的。”
宫兴赶紧说道:“是的是的,她其实也很可怜。”
果然,水华把帮助入画当作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她想了想,说宫兴道:“署名是贫下中农,理应请贫协主任先签名才好。”
宫兴眼睛一亮,可是转瞬间,他突然又是一愣,大家好像也和他一样,像是发现什么地方不对了。
水华掏出了昌翔的信给大家看,一边幽幽地说道:“这样说吧,我一直说卫超凡是坏人,不外是他破坏我和昌翔的结合。可是,假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昌翔这个人,卫超凡还会显得坏么?那样,我说不定一开始都不会拒绝卫超凡的求婚……现在,我就当世上压根就没有过昌翔这个人……”
说着说着,她竟悲从中来,强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却再也说不下去了。
瑶菁捏了小楚一把 ,朝大家说道:“你们还有事,我们走了啊……”
她又拉着姚铃儿的手说道:“你也跟我们走吧,到我们村另找个女婿,水军都不想在水库干了,你还跟他……你别笑,你想说你不会嫌贫爱富,对吧,可水军是个糊涂蛋呀,她说不定会嫌美爱丑的,说不定哪天犯了迷糊,蹬了你甘心娶个丑八怪大麻子……”
姚铃儿忙说瑶菁道:“说你是‘小妖精’,还真不假,你咋啥都知道?他……水军他竟当着我的面和那个哑女秀秀……”
众人都吃了一惊,莫不直愣愣地瞅着水军,水华妈绰起笤帚就打水军,一边怒道:“小畜生你 敢!”
姚铃儿赶紧挡在中间,水华妈趁势放下笤帚,揽姚铃儿入怀,轻拍着她说道:“我娃乖,有什么和妈说,妈替你作主,妈给你出气。”
姚菁笑着说姚铃儿:“小醋坛子,水军有了你,咋能花心。那你和水军都去我们家玩啊。”
姚铃儿笑道:“以后有机会再去嘛。我想和水军连夜赶回水库,他都离开好几天了!”
她一边说,一边看着水军。水军暗道,你们几个真是表演天才,没有脚本,没有排练,却配合得开衣无缝,把握得恰到好处,表演得维纱维肖,你们这样一做作一闹腾,又人多势众,我就算再想说什么,顶个屁用。便讪讪地说姚铃儿道:“都向着你,我以后可有罪受了。”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水华爹一直忙着在做晚饭,赶紧说道:“吃了饭再走,我可做的是大伙的啊。”
水华一家子都挽留,可小两口执意要走。宫兴家里冷锅冷灶的,如果也执意要走,就有些欠礼数了,便留在水华家吃晚饭。
吃完饭,天也黑了,姚铃儿要和水军走,水华妈笑道:“妈能让你黑夜辛苦赶路么?一百个放心,你姐马上就要去见卫贫协了,虽然是求他办事,老汉也会喜欢疯了,超凡他爸就算不再给水军添些好处,也决不会给他小鞋穿的。至于开除嘛,没影子的事。”
说着,她看向水花,水花便和宫兴一起去找卫贫协。
水花的到来,卫贫协简直乐到姥姥家了。只是她叫那一声“贫协爷爷”,老人家还是觉得有些美中不足。要是能去掉“贫协”俩字,他会更喜欢的。
要是别的年轻人只叫他“爷爷”,他还会觉得太“单调”呢,因为他很看重自己大队贫协主任这个头衔。
可是对水华,那就另当别论了。
果然,有水华出马,大是不同。当宫兴和水华如此这般地讲了事情的原委,卫贫协只气得真想骂宫兴窝囊废,但还只得装作笑眯眯的样子,拍拍宫兴的肩膀,说道:“小伙子心肠真好,以德报怨啊,能做到这一点,真是难得,难得!”
说到签名,第一个找的是他这个贫协主任,老人家自然当仁不让。他虽说识字不多,签个名却不成问题。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接着又叫过孙子卫超凡,叫他第二个签了名。
接下来,可想而知,签名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也会有临时出现的情况,宫兴就请水华拿主意。比方说,署的是贫下中农,那中农还让不让签?水华不假思索便道:“当然要签,还不能贫下中农在前中农在后,除了地主富农‘四类分子’,挨家一次过完。”
因为加上了中农,水华便又在“贫下中农”后面加了个顿号,再续上“革命群众”四个字,宫兴在心里直叫好。因为凭他那脑子,就算想到要加,也至多加上“中农”两个字,相形之下可就逊色多了。
下面进行得一帆风顺,这宫兴,村子里几乎各家都使唤过他,本村的,无论哪家请宫兴为动物割骟,他都分文不收。这水华的接生更是乖乖不得了,就算还没请过她的,以后呢,谁不信奉多子多福呢,真巴不得在以后的岁月里,能有幸多请她几回。
这样有面子的两个人大驾光临,大家自然言听计从。也有的人爱说话,也不过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几句,以示关心。多数是听了个一知半解,便全家都签了。不到两天,便接尽尾声了。
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事儿却在宫兴最好的朋友面前遇到了绊儿。
还不是五队猪场的那个余六指?他问这问那的,待详细地了解了来龙去脉,却说宫兴道:“我说呀,你把你那个入画叫回来,她只要迷途知返,村里人还会和以前一样,不会轻视她的。那个岑晨耀尽管对她垂涎三尺又大权在握,但总不敢公然到咱村来抢人吧。”
水华一怔,望向宫兴,宫兴不假思索地说道:“入画够伤心的了,咱们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还不知能不能帮她渡过难关,又怎能乘人之危……”
余六指怒道:“乘人之危?她本来就是你老婆,被那个鲍老师拐骗,没能享上福,反而遭罪。你们破镜重圆,对鲍老师也有好处。那个岑晨耀对入画彻底死了心,自然会把鲍老师放出来。”
宫兴马上道:“可是,如果岑晨耀恼羞成怒,变本加厉,鲍老师被迫害致死……”
余六指怒道:“死了活该,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他就算死一百次,也不会把你定为杀人犯!”
宫兴想,他不签也就算了,可余六指却把红布收了起来,说道:“你们居然肯花这样的笨力气找上千人签名,还不如说服入画,让她回心转意……嗨,我也情愿随你们一齐去的。”
水华见陷入僵局,她也知道这余六指就算说破嘴唇,宫兴也不会给入画出这样的难题,便说余六指道:“说真心话,我非常羡慕你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你对宫兴的关爱,我感同身受。你的建议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人各有志,咱们还是遵从宫兴的意见,你说呢。”
余六指长叹一声,边签名边说道:“我如果说你们是疯子,你们说不定肚里暗骂我是疯子呢。”
他想到那回“赛鹿”要和“黑缎”交配,卫超凡差点一脚把“赛鹿”踹死,还要马上杀了“赛鹿”,自己也曾大骂卫超凡是疯子,但后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却不得不佩服卫超凡的智计高人一筹。
他终于笑了,说道:“我比你们两个,是少数;比起这上面签了名的上千人,更是沧海一粟。好了,就算是少数服从多数吧。”
当入画从宫兴手里接过这签了一千多名字的红布时,竟泣不成声。宫兴说道:“如果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
他赶紧转身走了,因为她接过红布,便珠泪纷落,滴落在红布上……她眼里流出的是泪也是血啊。
宫兴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又回过身来,大喊着追上离去了的她,说道:“你展开这红布照张相,多洗几张,保存好底片,以防万一。”
她热泪长流,只是频频点头,哽噎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原来,苹果估产并不像粮棉估产那样精确。像满月这样的大行家,给屏底一队果园的晚熟品种估产也不过才十万出头,但结果产量超过了十六万!
当时的缴公粮,小麦价每斤才一毛二,但苹果呢,竟高达两毛。要说亩产,小麦不过刚“过黄河”,也就是五百斤,而苹果亩产竟能高达五六千。可见一亩园十亩田的俗语,并非信口开河。
鹰击公社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葛茂盛便凑到表哥周济跟前,悄声说道:“想请昌翔到我们济泉洼帮个忙,规划个 果园。”
周济笑道:“这哪有不行的?前几年你们如果也建果园,现在收益只怕要远远超过我们。”
葛茂盛知他说的不错,屏底一队人均耕地不到三亩,可他们济泉洼呢,人均五亩还多。就这,还有不可小觑的“埋伏”呢。当然,也不是说葛茂盛故意欺哄上级想少缴些公粮,而是山里的土地很少有像平原上那样长方形的,以不规则形的居多。这样,不论是丈量还是计算,想精确是万万不能的,人们习惯上总是赶少不赶多。
周济又道:“不过,你还得亲自找昌翔说去……”
葛茂盛大喜:“自然我还要去请他,单指望你派他去,像什么话?”
散会后,葛茂盛便来到了屏底一队果园,他原想昌翔不会拂他的面子,想不到昌翔竟好像比他还急。说道:“你先回,我随后就到。”
葛茂盛笑道:“也不急,你准备准备。持久战啊,别打算应两天卯就开溜。”
昌翔点头。葛茂盛哪里知道,水华就要结婚了,她要嫁卫超凡,昌翔正思谋着如何躲开。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简直是刚打哈欠就有人送上枕头,最好不过。
果然,第二天,昌翔就来到了济泉洼。
水华请谁当“逆姑嫂”呢,彩彩和满月!这“逆姑嫂”嘛,也就是市里说的伴娘,“逆”者,迎接之意也。
水华请彩彩时,彩彩脸倏的红了,水华这哪是暗示,简直就是说白了呀。
——水华不得已而嫁卫超凡,她想给昌翔一个交代和安排,给彩彩一个“重托”。
还有满月呢,水华不能有任何的偏袒呀。
别说水华,就是菩萨神仙,要做出二姝中谁嫁昌翔的决定,也会一筹莫展的。
水华请满月时,满月百感交集。水华的“重托”,也是她的心愿啊。
她即便能使出浑身解数赢了彩彩,但也不可以这样做!退避三舍吧,又诚非所愿。
命运之神竟是这样的促狭,尽管昌翔堪称机智果敢和多谋善断,但降临在他身上的,却总是天下第一难的选择!就算是萧何重生,张良再世,怕也难免举棋不定,首鼠两端!
水委会主任的公子结婚,自然是宾客如云,热闹非凡。鹰击公社各机关的人都来了,屏底大队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宾客们看到彩彩和满月在两旁扶着水华莲步轻移款款而行,都认为这是平生见到过的最美丽的组合。
他们就算能体察到水华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痛苦内心,但他们能猜测到彩彩和满月笑意盈盈背后的彷徨无计吗?
(未完)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百合花2013年1期频道
| 百合花2013年1期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