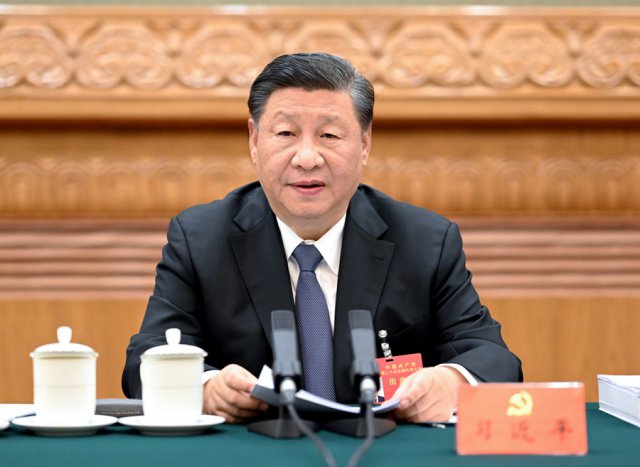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它象一头脊背穹起、昂首欲跃的雄狮,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越过青、甘两省的崇山峻岭,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奔腾晋陕之间的高山深谷之中,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的潼关以北来了个巨龙摆尾,调头向东,蜿蜒而去。它,既是一条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自然河,也是一条孕育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
悠久而神奇的千年古渡——茅津渡就坐落在黄河中游、中条山南麓的黄河岸边,它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为黄河三大古渡。三大古渡中,茅津渡为最。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茅津渡其名由来已久,多经更变。春秋至西汉时期,一直沿用矛槽沟口的称号,隋朝改为河头镇,唐贞观年间街道拓宽,商铺林立,遂命名为河头街村。后因老县衙并入河头街村,又复命为河头镇。明洪武年间,渡口改为矛津渡。时值大迁移,从洪洞迁移来8000余人,村南北就有4.5公里长,村境周长17公里,“商贾云集,店铺纵横,古物生辉”。后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茅津渡。茅津渡又叫“陕津渡”。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云:“陕城北对茅城,故名茅亭,茅戌邑也,津亦取名”。一个渡口,两个名称。黄河南岸的河南叫会兴渡,北岸的山西叫茅津渡。但会兴渡没有茅津渡叫得响,可能是这个渡口对山西更重要的缘故。据《平陆县志》载:茅津地当水陆要冲,晋豫两省通衢,冠盖之络绎,商旅之辐辏,三晋运盐尤为孔道。茅津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宋代诗人魏野曾赋诗《茅津渡》曰:“数点归鸦啼远村,人行欲尽夕阳路,暮霭还生竹坞村,西风乍起茅津渡”。茅津渡作为转运枢纽,为晋南的盐、煤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各地。
茅津渡——地形险峻,兵家争宠
茅津渡口两岸悬崖峭壁,河道瘦窄,水流湍急,若据有茅津渡口,则可以横渡黄河天堑,东通豫北,直至河北和山东;西达陕西,直通西安和大西北。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假道山西的虞国(今平陆县),由茅津渡过黄河,伐灭了河南的虢国(今河南的陕州),回师途中顺便灭了虞国。成语“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典故就来源于此。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伐郑,晋出奇兵从茅津渡河,以逸待劳,大败秦军于崤山。公元前624年,秦军从这里北渡伐晋。东汉末年,亡国之君汉献帝刘协由此仓惶北逃。唐朝“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为平叛,借回纥(he)兵3000人,也由此跨入中原。明崇祯15年(1642年),李自成大军到河南,河防戒严遂设游击驻守茅津镇,建“平垣营”。清时,平垣营额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名。辛亥革命时,秦陇豫复汉军两次东征,在渡口附近与清军激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该渡口成为转移我地下党员,保存革命力量的要道,也是抗击日寇和打击蒋家王朝的战略要冲。1939年,为抵御日寇北渡黄河,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属下第31军团(后改编为国民党第二战区第4集团军)司令孙蔚如总部驻扎东延,部下第38军军长赵寿山率部就驻扎在茅津渡及以东沙涧,死守渡口。同年6月6日,日军主力首先沿张(店)茅(津)公路南下,双方发生激战,伤亡惨重,防线在7日被敌人突破,8日日军攻陷平陆,10日占领茅津渡。1946年10月,解放军太岳军区58团由该渡口南渡黄河穿插国民党统治区,到伏牛山区接应新四军5师。1947年8月22日,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在茅津渡和济源长泉渡之间,乘“油包”强渡黄河三天三夜,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月歼敌3万余人,威逼潼关。1949年6月11日,解放军18兵团178师渡河进军大西北、大西南。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震撼全国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故事也发生在古渡两岸。
茅津渡——南北通衢,商贾云集
茅津渡口历经数千年发展繁衍,繁荣至盛。清朝以来至1938年日寇占领以前这一段时期,是茅津渡的鼎盛时期。清朝时,茅津村几乎家家都有生意人。英国人在茅津渡开了一家打蛋厂,光厂房就有170间,从全国收来的鸡蛋蛋青和蛋黄经人工分开后,用火烘干,然后装箱上船过渡口,运回英国。很多村民都在英国人开的厂里打工。工钱较高,村民们赚到钱后再拿去做生意。1936年的茅津渡,是个有着近万人的大镇。镇上有大小商铺300多家,河东杨家永泰昌的车马大店仅骆驼就有3000多头,商号发展到了蒙古一带。商人魏登科开了一家专新店(百货商店),足有一条街那么长,里面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浴华池大澡堂、官烟店、电话局、盐窑、烟厂、镖局以及各种小吃店一家挨着一家。每日清晨一片热闹的叫卖吆喝声,直到夜色降临吆喝声不绝。“旧社会这里比平陆县城(指老县城)还热闹,光商人就有340多户,钱庄、布庄,卖小吃的、卖烟叶的,卖什么的都有。那时货郎没有车,都是挑着货郎担坐船去河南卖”。茅津村老住户,今年82岁的王定华老人回忆。“那时从运城过来的路都是土路。人走、马踩、车拉,有时还有铲粪的,年头长了,走出一条槽来,比原路面低二、三米。”另据村民许金升老人回忆:1936年他7岁,。官府有800多人守着渡口,称作“由检营”。渡口有三个高等学府,一个女子学堂。龙王庙也不知建于何代,三进院落,双层木结构,都是木雕彩绘,华丽非凡。因村子大,排水就成了问题,明代有匠人在龙王庙下修了200多米长的石洞。石洞全是由青蓝色的方石砌成,洞壁两侧皆有图雕,雕刻精美,内容有《西游记》、《八仙过海》等故事。我们小时候经常下去玩,边玩边看,现在那些图案还清楚地刻在心里。随着龙王庙被毁,石洞坍塌就被埋在了河底……村里还有个祖师庙,也是修得富丽堂皇,三进院,还有一处偏院。最为称奇的是祖师爷爷在木楼下,祖师奶奶在木楼上,父辈们说这里还有一段佳话哩。村北门还有一座大禹庙,不知建于何年,父辈们讲是鲁班爷造的,正殿修有三个拱斗。鲁班爷临走时还留下几句话:“胜我者,缺斗三个;不胜我者,余斗无数。”意思是说他的技艺高超。许金升回忆,村里面庙宇建筑手法超群,全国知名。祖师庙四根通天木柱高20米,粗3米。大禹庙里有水浒和包青天故事等雕刻,皆为玉石雕就,光彩夺目,非常珍贵。后殿有一尊佛,皆为银圆砌成,石碑记录用料三百万两银圆。庙里还有一尊五色玉石的娘娘像,价值连城。另据原村民(日寇占领茅津渡后迁居东延)姚有福老人回忆:1938年日寇占领前的茅津街异常繁华,四周皆有城墙,四个城门经常有人把守。涧东、沙涧、东延以东的人一般从东门进;北门又有大、小北门,从小北门出往西去老县城,出大北门直通张茅路;南门紧挨渡口。城门外还有南头沟、东沟、芝麻沟等村子。城里分上街和下街,上街全是商铺,下街是居民区。他听老人们讲,他们家就是从洪洞迁移过来的,在此也居住好几百年了。他家就在下街的第三家,北面紧挨着商铺,街上的叫卖声、酒楼里的划拳声,声声入耳,清晰可辨。每逢春节、元宵节,茅津街热闹非凡,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灯火辉煌,通宵达旦,灯火照亮了整个黄河,河水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庙宇戏楼,鼓乐铿锵,丝弦悠扬,好戏连台,人们陶醉在欢乐之中。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以后,茅津街惨遭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蹂躏,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茅津人四处逃生,茅津街顷刻间变成了一座燃烧着的死城。昔日车水马龙的渡口没剩一只木船,茅津街几乎被夷为平地。1942年前后,驻守在东延一个连的日本鬼子为了解决生活取暖问题,经常派苦力去茅津街将未烧掉的房屋木料拆卸下来运回东延据点,以供他们当柴火用。《平陆交通志》记载:1936年,有400多口住户的茅津渡是黄河流域有名的水旱码头。专营潞盐的盐窑就有9家,经营百货的京货铺就有8家,另有杂货铺、药铺、饭店等。1940年,日军侵占平陆后,烧毁木船和渡口百余间房屋,茅津渡沦为废墟,解放后才得以恢复。
重铸辉煌,再展风采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部分茅津人返回家乡,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渡口。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连年内战,加之村民们饱受战乱之苦,元气大伤,茅津渡已今非昔比。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茅津街人为了我人民军队渡河抗击日寇、消灭蒋匪、解放全中国,他们不惜家产,伐树木、拉木料,为渡河大军打造船只;不惜生命,顶枪林冒弹雨,掌舵拉纤,护送大军渡河。他们舍生入死,功不可没。解放后,成立了人民公社,组建了新的村委会,茅津街村集体购买了9只木帆船,渡口开始复苏。1958年,平陆县政府成立了航运站(1980年更名为航运公司),载重30余吨的木帆船在渡口唱起了主角。上世纪70年代,茅津渡先后建造了两只木质平板船和一只拖船,开办轮渡汽车业务,当地人称“自动波”。一开始全县的汽车没有几辆,后来慢慢多了,生意也就好了。在木船上加装了柴油机动力,从此告别了扬帆起航和撑篙拉纤的远古时代。他们往来晋豫,主要运输棉花和粮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物流急速加快,位于209国道张茅段的茅津渡码头必须要扩容改造。县政府审时度势、顺应形势,于1980年初首先对渡口码头进行大规模修整,码头石砌平台,道路水泥硬化。其次,投巨资(争取省厅70万,航运公司自筹10万)请湖北船舶修造厂倾力建造了一次能过渡12辆载重汽车和300名旅客的大型钢制渡轮——晋航一号。该渡轮耗资相当于当年100辆解放牌卡车的价格,船总长49米,宽18.5米,。1981年3月晋航一号正式启航,昼夜穿梭在茅津渡和隔河相望的会兴渡之间。此渡轮属于客货两用船,既载货车、客车,又载客人。一辆客货车船票为30元,客人每人一元,即使片刻不停地营运,两岸渡口的车辆还是排队长达2公里开外。那时渡口边就是209国道,是山西到河南的主要干道。县航运公司拥有职工80余人,一天的营业额多达2万余元,效益相当可观,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85年县政府又出资打造了晋航2号钢制渡轮,此船可容纳10辆大车。在县航运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船工王应照说,这两个大船当时是用军工设备建造的,加油挂档都是电子液压配合操作,至今不落伍。“茅津渡的两艘渡轮,是当时黄河中上游最先进的。那时公司在当地国营单位效益最好”。平陆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仵亚平如是说,“80年代,公司每年上缴利润二三百万,最高峰在90年代初,一年缴了470万元。”上世纪80年代以前,茅津渡口的硬件设施没啥大的变化,延续了几千年来的水上交通工具——十多只木帆船,后来发展为木机船,此木船只能承载货物和客人,而且只限白天通航,“黄河自古不夜渡”。1980年以后,随着茅津渡的扩容改造和两个大型渡轮的先后启用,渡口水运能力大大加强。航运公司的几十名职工三班倒,昼夜摆渡,打破了“黄河自古不夜渡”的老传统。当时的茅津渡口设有派出所,专门负责维护渡口的治安工作。南来北往的车辆、客人络绎不绝,待船的车辆一字排开,首不见尾。有的货车司机为了赶时间不想排队等,就找关系托熟人。茅津村的一些老头、老太,手提小竹篮和小耙耙,在路上拾煤车上掉下来的煤块,有个别的趁人不注意便用小耙耙撸车上的煤。沿路两旁有好多商铺饭店,车辆排队待船,做小生意的便提着小篮子逐个车推销,叫卖声、汽车喇叭声、大船汽笛声,不绝于耳。晚上的渡口,灯火辉煌,依然繁忙,如同白天。
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儿时记忆中的茅津渡模糊不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缺吃少穿,物品供不应求,就连肥皂、火柴、布料、牙膏等一般日用品都要凭票、证购买,像食品之类的东西在县城有钱也买不得,县城仅有的二、三家国营饭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天营业不了几个小时。那年的初冬,冷风嗖嗖,听说三门峡市(因三门峡大坝而刚建市)有卖吃的,爷爷就带我一大早和乡亲们一起,从我们村南黄河边乘小船往茅津渡驶去,当时三门峡大坝已关闸蓄水,只记得河面宽阔,水面悠悠,碧蓝而平静的河水好像是一汪湖水不见流淌。由于船小人多,水面几乎与船沿相平,我坐在船边伸手就可摸到河水。我们把小船停靠在茅津渡的对面,从会兴渡步行到市里,大家不进百货店,只进饭店,饭店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排队买吃的。由于饭店挤满了人,没处坐,只好站着吃。我与爷爷饱餐了一顿,回来时还带了几个小包子。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串联,我随同学到三门峡市逛了一圈,大部分同学上火车前往全国各地,我和几个年龄小的同学返回,怎么坐船过去又怎么回来,至今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但肯定是茅津渡。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村子里务农,曾两次去茅津渡。一次是挑上筐和生产队的年轻人到渡口的船上卸煤。当时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生产队从河南焦作定购的混合面煤,拉回家,掺点土和成煤饼,以供取暖做饭用。一次是冬天生产队派我们两人牵上小毛驴拉上小平车从西延、枣沟河滩,穿越茅津河滩柳树林到渡口去拉煤,直线距离10华里不到。
上世纪80年代初,去茅津渡的机会就多了。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平陆中学、县委党校、县委办等单位,因去三门峡市逛,茅津渡是必经之路,但一年也去不了几次。一是工作比较忙,二是交通也不方便。当时从县城到三门峡,先骑自行车或坐客车到渡口、再乘船、下船后再步行或坐车,才能到市里面。往返一来回,倒六次车、船,加上等车、船,大约得近三个小时。所以没事一般不去三门峡。记得最清楚的有三次:前两次是80年、81年夏暑假,学校组织部分教师乘两辆小嘎斯车去华山、西安旅游,经过茅津渡。还有一次是1991年深秋,带妻携子全家四口人过茅津渡去峡市,在峡市街心公园还留了影。
有喜有乐,有愁有悲
茅津渡虽然繁华热闹,但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据我所知有两件事:一件是在1985年暮秋的一天,东延有三个人去峡市办事,经茅津渡到会兴渡下船,坐上河南拉人的小机动三轮车,由于岸上的坡陡,司机在行驶中没抢上档而连人带车退到河里,司机见势不妙跳下了车,二人落水溺死,一人获救。另一件是1990年秋天,正是秋收季节,运城地区客运公司一客车拉一车人从运城到茅津渡口,欲渡河去河南,停在岸边等待上船。此时,有一部分人下车买东西,还有20余人在车上,车停在岸边的陡坡上,由于刹车失灵,司机又不在岗位,客车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车就一下子冲向河中,据听说车里还有一位乘客是我县张店的。此时的河水浊浪滚滚,流速很急,河水即刻将客车吞噬。为了打捞落水者,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积极营救,还请来青岛等地的专业打捞队、潜水员,在河中打捞了一个多月,每天前来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但由于河水浑浊,流速又快,潜水员纵有千般本领也派不上用场。最后还是航运公司的船工在下游500米处,放下大铁锚来回拉动,才把大客车钩了上来。车内存留部分人,部分人被河水冲走。数月后,在渡口下游的河滩上不时晾出一、二具死尸。一次据沿河群众报告,我们县委办的几个同志和时任县委书记霍转业及公安局长与法医前往枣沟河滩,发现是一具女尸。由于河水长期浸泡,尸体虽未腐败,但四肢严重肿胀,衣裤撑得紧绷绷的,法医从其身上发现有关证件,她原是万荣县一家机械厂的厂长,属于该事件的受害者。我们立即通知了当地的有关部门。
自1993年三门峡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便终结了黄河两岸靠船摆渡的历史,茅津渡悄然退出一线。它被列入战备渡口,每年由省交通厅补助20万元。现在的航运公司已名存实亡,部分职工安排到黄河大桥管理处工作,其他人仍无业可就,茅津渡从此一改往日的喧嚣热闹,寂寞萧条,繁华不再。十多年来,随着三门峡库区管理局治黄力度的不断加大,茅津渡东西1000米沿岸皆用石头砌成坚不可摧的护岸石坝。石坝上栽满了垂柳、梧桐、冬青等花草树木,渡口及周边的环境大为改观。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渡口的命运,很少有人到此光顾,“门可罗雀”代替了原来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整个渡口死一般寂静,唯有两艘渡轮还依旧巍然屹立在渡口岸边,俨然两位守护神昼夜坚守。1997年前后,航运公司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曾将“晋航一号”轮渡整体承包给西安一客商,该商家把轮渡装扮一新,在船的一层装隔了若干个小包间,可唱歌、可休息住宿、可用餐。二层搭上凉棚,四周护栏,供游客观赏。每年蓄水季节,游客可乘船上到黄河大桥,下至三门峡大坝。但由于游人少,生意做了没多长时间就不了了之。近几年来,也有茅津人利用黄河蓄水季节,买了十多只小汽艇放在河边,以此招揽游客。每逢春夏两季,尤其是夏季,天气酷热,县城里的人们下班后,或开车、或骑摩托,三五成群来到渡口边观观景、乘乘凉。这些年来,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到渡口,一看如此这般,便高兴而来,扫兴而归。随着时间的推移,千年茅津古渡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慢慢远去,它将成为历史的记载和人们的记忆。再过若干年,茅津渡恐怕就会被人们彻底遗忘。
千年古渡落得个如此下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出现如此的情景又是意料之中的事,大可不必眷恋惋惜,千年古渡的衰落,反倒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从茅津渡的变迁,可以反映出我们国家实力的强盛,交通事业的发达,人民生活的富裕。现如今,蜿蜒数千里的黄河两岸数十座大桥横跨南北或东西,天堑从此变通途。人们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早在1986年3月,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第一次会议上就正式申请提出三门峡黄河大桥项目,1991年11月中铁大桥局正式施工,1993年 9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为大桥题写了“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的桥名。1993年9月30日大桥合龙,12月30日剪彩通车。三门峡黄河大桥北起平陆县蒿店村,南至黄河三门峡市湖滨区后川村。全长1310.9米,正桥桥面总宽18.5米,其中车行道宽1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5米,它是国道209线(呼和浩特——北海公路)连接晋豫两省跨越黄河天堑的特大型桥梁。大桥总投资1.2亿元,山西在大桥和北引线6.1公里共投资9160万余元。大桥的建成通车,对加强交流、发展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方便了两岸群众,加强了两岸交流,发展了两市经济,为晋陕互通有无两省尤其是运城和三门峡的经济腾飞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前又有好消息不断:运(城)三(门峡)铁路项目已报批,总投资60个亿,其中在平陆县张裕村建造客货站就斥资4个亿,不日即将动工;老城至河对面的陕州县城西建一座黄河铁(公)路大桥;运(城)芮(城)——灵宝黄河公路大桥,打隧洞、钻中条,在芮城和灵宝之间架大桥;平陆县东沿河公路拓宽改造工程,争取投资4.3亿,春节后即可开工。这些消息令人欣喜,催人奋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强盛、经济的高速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日新月异,黄河两岸的亿万群众将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百合花2013年1期频道
| 百合花2013年1期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