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些以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书写的大字标语,在我的小时候,在房前屋后或路边的大墙上,在大队部、马坊、库房等公共场所的内外崖面上,在记工室、学校教室、农民夜校里的墙面上,在家家户户的板门和风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至今,在一些老村子里还留有许许多多的遗迹。这些,只是一种形式,还无所谓,真正厉害的就是记忆中的大批斗了。
那个时候,无论你是成份不好,还是做了坏事,甚至说错了话,都可能成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专政对象,都会挨到批斗的。大批斗,小则开个群众会,自己做检讨,大家做批评。大则站在下面满是群众的大会前低着头,听着大家言辞犀利的批斗。再大一点,要么戴个用竹编的防治牛干活吃庄稼的嘴罩子和芦苇杆子做骨架,外面糊上白纸的高纸帽,胸前戴一块废纸箱剪下的糊有白纸写着罪名和姓名的长方形纸牌,要么两个人在后面扭着胳膊,要么用绳子把双手绑着牵起来,喊着口号、敲锣打鼓、沿街走村串户游斗。要么站在准备好的高凳上、架在一起的桌子上,进行批斗。要么背扛所谓的赃物、胸挂纸夹夹着的赃款,站在公社的大舞台上,亮相批斗。反正这些手段,我都觉得挺害怕、挺残忍、挺无人情味的。
记得当时我还没有上学,一个早上的10点钟前后,我的西头门前,前面两个孩子扭着我自家的一个大姐,后面跟着两队学生,最后跟着老师,它们打着锣鼓,喊着随口编来的“翟某某,脸皮厚,机关枪,打不透!”口号,游斗我的大姐,可大姐那是还是个小学生,至于犯了啥错,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说不来是贪玩不听老师的话吧!
记得有张姓的老两口,因为成份不好,怕人多惹下了是非,干脆住到了只有他一户人家的北头沟,就这也没有逃脱挨批斗的厄运。老婆个子不大,是个小脚,我们一直叫他张老婆。或许是批斗没有对象吧,那天在我村的官院批斗她,我自家有个有点二的哥哥,把站在会场前的张老婆按的腰躬的足有90度,左手扭着张老婆的胳膊,右手攥成拳头狠狠的一拳一拳砸向张老婆躬着的脊背,每砸一拳,张老婆都要撕心裂肺的“啊”一声,眼睛都有眼泪流出。我的“二”哥说“叫爷(方言读ya)”,张老婆喊一声“爷(方言读ya)!”我的“二”哥说“叫奶(方言读nue)”,张老婆喊一声“奶(方言读nue)!”那残忍的场面在我幼小的心灵烫上了深深的烙印。
记得我自家有个老哥,也是成份不好,最早住在寺沟的刘家洼,他的院高处的梁顶是日本人驻扎的炮楼,日本鬼子每天逼迫幼小的他从沟里给炮楼送水送柴。就因为这,村民在他刘家洼的老宅挖地三尺寻宝,在南头崖(方言读lai)场批斗他,他是个秃头,头顶常年裹着一条羊肚毛巾,批斗他的人用竹竿挑掉毛巾,把他的秃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把他站在脚下两个架起来的方桌掀翻,让他从近5尺高的桌上硬生生的一次又一次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
记得我村附近的中学里有个姓姜的老师,不知啥话说错了,也不知是啥课讲不对了,有一天一队人马游斗他。他头上戴着白纸高帽,身上糊着的白纸上写着“牛鬼蛇神”,后面跟着的人用扫帚在他身上扫着。他两个手腕在胸前被麻绳缠住后绑在一起,左手掂着一个铜锣,右手拿着一个木制的锣锤敲着。因为两只手距离间隙太小,鼓不上劲,敲着敲着就没有锣声了,游斗他的人就喊鼓劲桥,这时你听到的“咣、咣、咣、咣......”的锣声就会一声比一声小、一声比一声紧,最后干脆就没有声了。那个痛苦的折磨,想着也是相当难受的。
这样的群众批斗会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虽然感到无情、感到残忍、感到也有人借机泄了私愤,但是那时把人整的挺有觉悟的,有人深夜起来把一堆粪担到集体地里没人吭声,有人无意把收音机调到了“美国之音”还怕人监听,村里的苹果和西瓜没人看也没贼敢偷。根本不像现在,廉政、廉洁、遵纪、守法喊得那么厉害、抓的那么紧、管的那么严,该腐的还腐、该贪的还贪、该犯的还犯,就是把快刀利刃架在脖子上、把高压电线绷紧脑门顶、把烫手山芋捂在胸口间,也有人“大义凛然”、铤而走险、“在所不辞”。红红脸、出出汗的刮胡洗脸式批评已经不见效了,必要的伤筋动骨的批斗还是会有结果的。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你死我活”斗争,斗争出自觉性、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只有斗争,才能锻造一支拉得出、作风硬、战得赢的大公无私的、廉洁自律的、敢打胜仗的、群众信任的队伍。(翟战功)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 文化旅游频道
| 文化旅游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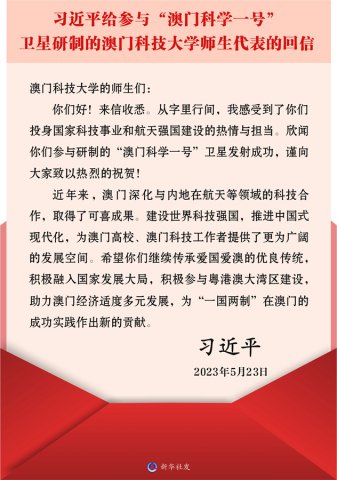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84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840号│






